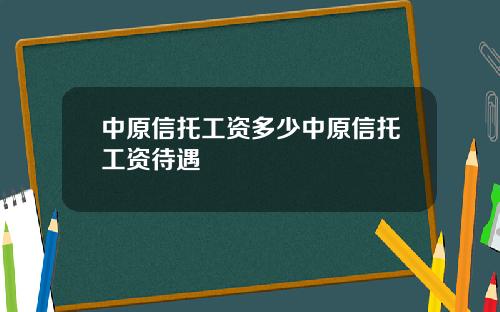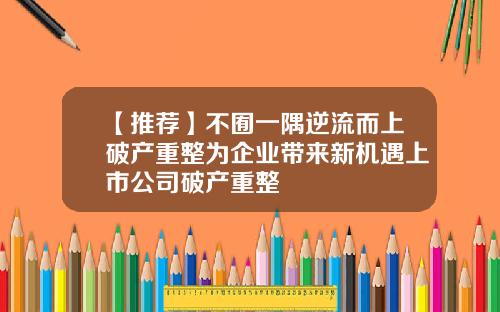文章目录:
1、清华园的「女先生」2、又上热搜隔着玻璃晒太阳,到底能不能补钙?3、曾经的北京宣武,你还有印象吗?
清华园的「女先生」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我们想动情讲一讲
清华园里“她们”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们光芒四射
我们称她们为
清华园的“女先生”
她们才华横溢,怀揣梦想
她们爱国奉献,温暖善良
她们的故事生动纯真
如同这个美好的春天一样
当年,她们如何在清华园学习生活?
又有怎样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
让我们走进岁月长河
从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女生开始
寻找她们在清华园留下的印记
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入校女生
早在1921年前后,清华内便有关于“清华男女同校”的呼声,然而仅议却未行。直到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罗家伦答应了此项要求,但是在他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过,于是罗家伦决定在10月份举行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清华的“女禁”自此开放。
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故曾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稀宝”。这批入学的同学被称为“第四级”,有同学专门写了首《四级级歌》:“春来大地兮遍紫黄,共坐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吾级始创,始创,始创,吾级之光。”
初招女生时,清华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女生专用宿舍建成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1932届校友欧阳采薇女士曾回忆:“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冬季成为天然溜冰场,离女生宿舍古月堂很近。那年冬季,我和黎宪初时常一起去溜冰。”
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于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就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女先生”。我们选取了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先生”,或许大家知道她们后来在各领域的成就,而她们当年和这个园子,却有说不完的故事……
林徽因:“她就是中国一代才女”
“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
这里是新林院8号,也是林徽因、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两位先生搬到这里,依然保留了北总布胡同时“午后茶聚”的习惯,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都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
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李健吾后来这样回忆道。这就是那个年代那群可爱人间的趣事。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林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院8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胡适曾说:“林徽因就是中国一代才女。”而见证与凝聚了一段传奇的新林院8号,也因与梁林夫妇、与新中国建设的特殊情缘,多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意义,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追思与遐想。
陆士嘉:爱国情深,质本洁来还洁去
清华园胜因院23号,记录了陆士嘉和张维这对为中国力学学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夫妇爱国情深的一生。
1946年,阔别祖国9年之后,夫妇二人回国。应清华大学钱伟长的邀请,陆士嘉和张维携子女于次年秋天来到清华开始他们的从教生涯,结束了他们漂泊的生活。
陆士嘉曾师从流体力学之父、边界层理论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是其唯一的亚裔女博士。因为“夫妇不能同时任教授”的不成文规定,陆士嘉到清华后先在水利系担任工程师,解放后被清华大学航空系聘任为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她和清华航空学院参与组建北京航空学院,她也是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在胜因院23号,夫妇俩过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简朴生活。镶嵌着周总理照片的银色镜框,是客厅里的唯一装饰。虽然自己过得相当简朴,但他们却经常接济亲朋好友和帮助素昧平生的人。十余年间,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幸福,家中时时传出欢声笑语。
夫妇俩都有着“一心报国,身先士卒”的品格。20世纪80年代,70多岁的陆士嘉仍然热心于生物流体力学的发展,并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条文。由于常年过度劳累,陆士嘉患上了心脏病。即使在住院期间,她还坚持审阅论文、指导学生,直至1986年溘然长逝。
2001年张维病逝,夫妇两人骨灰合撒于圆明园荷花池内,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
杨绛:淡泊澄明,唯留一颗赤子之心
清华早期的女学生之一杨绛,她的爱情故事,正是发生在清华园古月堂。
1932年3月初,杨绛与钱钟书在古月堂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杨绛后来在文章中写到:“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他们侃侃而谈,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50年清华校庆日,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瑗摄于新林院寓所。
杨绛“三进清华”和清华为钱钟书“两次破格”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对他们的女儿钱瑷来说,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杨绛曾说。
杨绛与清华同龄,冥冥中与清华结有不解之缘。她情牵清华、关爱学生,无偿捐赠母校并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她才情横溢,是许多人眼中百年罕见的“奇女子”,却又豁达简朴、淡泊澄明,唯留一颗赤子之心。她身上烙印着历史的年轮,完整而深刻地经历了中国现当代以来起伏跌宕的民族历史,仰赖高寿与丰赡的著述,使她成为百年历史最具画面感和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之一。
王明贞: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
她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6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她还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
她的名字叫王明贞,一生献身物理领域。
1954年,王明贞与丈夫俞启忠在旧金山手捧回国申请材料
刚刚回到祖国的王明贞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 “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她被教育部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她十一年的清华从教生涯,她也成为清华大学最早聘任的女教授之一。
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贞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她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她平等地讨论。“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王明贞对自己十一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
王明贞和丈夫俞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贞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她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40多年了,几经她亲手修补,还算结实。
王明贞一生都在 “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何泽慧:“中国居里夫妇”的女主角
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与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环。”
何泽慧随身带了两元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来到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报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清华大学从1928年才开始招收女生,全校女生寥寥可数。物理系1932年入学的28人中,女生5名,非常惹人注目。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最终只有10人顺利毕业。毕业时,何泽慧毕业论文获得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就是后来的丈夫钱三强并列第一。
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为清华同班同学,两人都是爱国科学家
毕业后,两人分别出国深造。1946年,何泽慧与钱三强结婚。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二战后他的实验室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此时,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
何泽慧是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创者之一,她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常沙娜:永远的敦煌
她的名字是里昂的一条河流。
她的根在敦煌。
出生在法国里昂索纳河河畔的常沙娜,受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父亲常书鸿先生影响,从早年起,就与茫茫沙漠里的千年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少女时的常沙娜,是这样跟随父母举家前往敦煌的——一个多月的卡车颠簸,半路冻得受不了换上皮袄毡靴,最后坐着木轮牛车抵达。寒冷与荒凉,是敦煌留给常沙娜的第一印象,但同样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常书鸿决意保护敦煌的积极和乐观。
1951年,常书鸿将敦煌研究所常年临摹的作品带到北京展览。常沙娜受父亲所托,陪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参观了展览,并由此结识了她在艺术设计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常沙娜作为林徽因的助教,与同事一起对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设计上的改进,融入敦煌的图案,也使之更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忆及这段往事,常沙娜说:“是林徽因决定了我将自己的终身献身给艺术设计和教学。”
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到宣武教堂彩色玻璃窗的大胆创新,从再现敦煌盛唐彩塑的香港志莲净苑佛像到呈现自然生命之美的花卉写生,常沙娜在数十年的艺术设计和创作中洒下一路芬芳。
常沙娜曾说:“要有思想准备,要奋斗,要面对现实。要爱国,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绝对不要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我们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的。”
钱易:教书+环保=一辈子
她在清华大学教了近60年的书。她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自从一脚踏入这个领域,就是一个甲子。她是学者钱穆的女儿,但她却从不希望自己被父亲的光环庇佑。
她是钱易,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写成厚厚的几大本书,也可以浓缩为最简单的一个等式:教书+环保=一辈子。
“做环境事业的人,有点像堂吉诃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虽然可能一生中都没有办法看到目标实现,但依旧不改初心。”
钱易与环境保护的缘分,已持续60多年。低耗废水处理、水污染监测、水资源保护、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她关注着这些问题,青丝变白发。
钱易的家,是广为人知的无锡钱家,素有“一家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美誉。她自小就在母亲的感染下,对当老师有了特别的热爱。
还有几位老师对钱易的从教影响颇深: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的胡家骏先生,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陶葆楷先生,以及清华大学的顾夏声先生。
钱易很谦虚,极少提起自己,唯独谈到学生时,话才会变多。“我跟学生关系很好,而且学生对我也很好。”钱易爱吃红烧肉,有一位学生就给钱易送过一碗自己做的红烧牛肉。“他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不过我们还像很久以前一样。”钱易笑着说。
钱易备课一丝不苟。课上,她总是笑眯眯的,一堂课讲完,连水都不喝一口。
“只要还有力气,还有精神,就不能从讲台上下来。”
朱凤蓉:惊天动地的青春化作灯火
朱凤蓉回忆,1964年10月16日,在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当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已经躺在床上了,就听到楼道里突然喧哗起来,我们当时立刻从床上跳下来,那个高兴呀……”
那天晚上,大家都聚集到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欢呼。作为工物系的同学,她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朱凤蓉的校友、未来的丈夫张利兴在毕业时丝毫没有犹豫,奔赴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等朱凤蓉毕业后,她也选择追随爱人和理想。那年她26岁,一个人带着两箱课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前往张利兴所在的部队。下了火车,还要在“颠得人能跳起来”的“搓衣板路”上,半蹲半坐半站地坐7个小时的汽车。
虽然艰苦,但他们义无反顾。曾经的空中核试验取样困难,空军驾着飞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蘑菇云,在烟云燃烧的短短几分钟里把物质取回来给实验员分析诊断。当时的仪器设备灵敏度不够,为了“对得起取样的飞行员”,朱凤蓉没日没夜地做实验。“连续作战下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白血球降到2000,眼睛白内障。”回忆及此,张利兴满是心疼。在青春埋藏的苍凉戈壁,他们依靠志同道合的默契给彼此温暖。朱凤蓉回忆说,“也不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有雪山,也有蓝天。”
“有机会参与到共和国的成长中来,我们是幸运的。”朱凤蓉说,“我们搞的是看不见的刀山火海,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是在大漠奋力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如今,从戈壁归来的张利兴和朱凤蓉,都已经成为了少将。这对将军夫妻,依然习惯简单的军人生活。那些惊天动地又隐姓埋名的青春化作灯火,留在记忆的远方。
陈薇:一见钟情,从容幸福
陈薇一直清晰记得,当年自己从清华毕业时的画面:“1991年4月,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一辆军车把我从清华园载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了我携笔从戎的军旅生涯。”
弹指一挥间,“如果说我今天做出了一点成绩,这是与当初的选择密不可分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结合得越紧密,得到的支持越大,发展的空间越大,个人才华就能充分得以展示,个人价值才能被高倍放大。”
如今已是“人民英雄”的陈薇,一直觉得她的另一个身份更令自己骄傲,“我是一个快乐的母亲,幸福的妻子,孝顺的女儿和儿媳。”
陈薇在清华读书时,有一年五一劳动节与同学相约去泰山,火车上邂逅了现在的丈夫,一见倾心定终生。
陈薇曾在儿子周岁的时候和他说:“你这辈子做好两件事就行了,第一是娶自己爱的人,第二个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陈薇对孩子说“我从来不奢求你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希望你是快乐的、健康的、富有爱心的”。
她始终认为,一个女人,事业再出色,如果家庭不幸福,那她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在工作中淡化你的性别,在生活中突出你的性别,睿智与亲和并存,执着与从容合一,出色工作,享受生活。”这是陈薇对幸福女人的定义。
与丈夫相识十年时,陈薇曾写过这样的随笔——
十年前,我与“一见钟情”的丈夫常常情不自禁地牵手相视而笑。十年后,十指相扣的默契依旧,笑嫣依然,只是相牵的手多了一双小手,而儿子灿烂的笑,更是我前进的源。
从清华园走出的这些“女先生”们
已成为一批又一批巾帼豪杰
她们中有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女英烈
有在科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有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
她们和所有清华学子一样
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前仆后继、无私奉献
多幸福,这座园子
曾目睹过她们的绽放
多幸福,这个春天
园子将迎来110岁的生日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动人的
清华园“女先生”的故事
在历史长河的光芒中
陪伴并激励我们
热爱生活,勇敢前行
来源:清华大学
又上热搜隔着玻璃晒太阳,到底能不能补钙?
天气凉了
有的人懒得出门
索性坐在自家阳台
隔着玻璃晒太阳
微博上的热搜
因此“不请自来”
↓↓↓
#隔着玻璃晒太阳
能补钙吗#
这届网友的回答
也是各式各样
有人认为这样补钙
是无效的
有人觉得应该
增加“剂量”谈效果
有人连带还提出其他问题
比如孕期补钙剂量
衣服穿得厚是否有效等
......
那么隔着玻璃晒太阳
是否可以有效补钙呢?
↓↓↓
专业医生们也都这么认为
↓↓↓
山西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医生高文莉:
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紫外线A、紫外线B和紫外线C。紫外线C几乎都被臭氧层所吸收,对我们影响不大。紫外线A有很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大部分透明的玻璃以及塑料。紫外线B大部分被臭氧层所吸收,只有不足2%能到达地球表面,它穿透力不强,会被透明玻璃吸收,但是紫外线B能促进体内矿物质代谢和维生素D的形成,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无法促进钙的吸收。
绝大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10-20分钟即可,儿童短些,老人长些,但一般都建议在30分钟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曹雪霞:
晒太阳的主要目的不是补钙,是补充维生素D。维生素D主要作用是促进肠道钙吸收,增加肌肉协调性,预防跌倒。紫外线晒到皮肤上,皮肤的7-脱氢胆固醇会将维生素D逐渐转化。隔着玻璃晒太阳会阻挡一部分紫外线,紫外线量会明显衰减,导致维生素D吸收受影响,也会影响钙的吸收。而钙,大部分则需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牛奶或者钙片。
隔着玻璃晒太阳确实无法促进钙的吸收,甚至还有可能被晒伤。如果实在是无法出去走动的话,也一定要打开窗子,让阳光直接与皮肤接触。“夏天短裤和短袖、冬天露出脸和手”就是最佳选择了。
正确的晒太阳方式
都get到了吗?
综合:上海科协、人民网
来源: 每日甘肃
曾经的北京宣武,你还有印象吗?
原标题《宣武门琐谈》
让土生土长的老宣武区人引以为自豪的宣武区,在2010年7月并入了西城区,虽然这里已更名,但宣武门这个地名永远地存在着。
老街“老墙根儿”
我儿时的家就在宣武门外的老墙根街,那时这里全都是平房住宅,我自出生后到成家之前都居住在这条街上。这条街道虽然并不宽大,但早年这里人口众多,很是繁华,尤其在早晚时,人群熙熙攘攘,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这条街上各种商店很多,生活用品齐全,足不出街即可买齐日常用品,可以说是一条“自给自足”的街道了。此外,街上还有一些著名的工业企业,如北京手扶拖拉机厂、衡器厂、日用化工厂等。文化教育的机构更是众多:托儿所、小学、中学,还有北京首家红旗业余大学。
老墙根是辽代就已经成名的一条老街,远比被称作北京最老,源自元代的西四砖塔胡同的历史年代还要悠久许多。老墙根街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条土路,它并不长,也不宽,只是位于北京南城的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胡同。那为何称作“街”呢,而不是“胡同”?要说明这些,就要追溯到辽代时期。辽代北京这个地方是辽王朝的一个陪都,是辽代五个都城之一,那时称作南京。其他四个陪都分别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的上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大定府的中京,今辽宁辽阳市的东京,今山西大同市的西京。
老墙根这里正位于古时辽南京城东的东安门城内城墙根处,故称作老墙根街,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胡同志(上)》中有详细具体的考证说明。如今菜市口南侧的西砖胡同口与广安门内大街相交叉处绿化带中还立有“辽安东门故址”的碑刻。而在《辽沈晚报》载有:“辽南京城的东城垣在今校场五条(与老墙根街东端交界)、烂缦胡同一线。”由此可知,老墙根成街确早于元代。
老墙根街并不临马路,但距离宣武门很近,宣武门城楼内外大街便是我们外出北行南往的必由之路。宣武门城楼城墙,城外的护城河,沿河向西的河沿岸(当地人称之后河沿)虽早已逝去,但我对这里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儿时宣武门城楼和城墙的景象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儿时的记忆是最牢固,最清晰,宣武门城楼城墙,城外护城河和街巷至今我历历在目。
说起宣武门城楼,我儿时眼中的城楼已是年久失修,很古老、很陈旧、很沧桑,斑驳的油漆粉饰已基本脱落。城楼呈南北向,城墙两端向东西延展,如今的宣武门地铁沿线道路就是当年城楼和城墙的原址。
宣武门城楼高耸,城门洞的北侧左右两旁城墙内侧依附着长长的、宽宽的登城楼坡道,沿着坡道向上可以登顶。我儿时的城墙并无管理,是可以随意登攀的,站在城墙顶端可遥望宣武门内外大街和周边的所有房屋建筑,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城楼下面的城门洞时而有车辆穿进穿出。宣武门周边基本是一些低矮的平房,很少看到楼房,更没有高层的建筑,以显得城楼是那样的巍峨,那样的壮观。
城墙外,紧邻护城河北岸是北洋时期建造的环城铁路,环城铁路是1915年6月破土,1916年1月1日建成通车。在铁路与城墙之间是露天堆场和散落的一些居民住宅。环城铁路沿线的城门外都有堆场,当年各城门外的堆场均有分工,宣武门铁路站负责的囤积煤炭和建筑材料。铁道两侧是一片片的货场,堆放着建筑材料和大面积的煤炭。再往南便是护城河的南段,水面宽阔,河水缓慢流淌着。
自宣武门城楼向南,跨过护城河上汉白玉石桥是宣武门外大街,街两旁有商业、工厂和学校,早于民国时期,这里还有众多的各地会馆。街东侧有万宝全百货商场、长城风雨衣服装厂、餐饮店等;街西是银行、豆制品生产厂、副食商店、邮局、信托商店(旧货)。宣武门外大街最南端是老宣武区最繁华的地段,商店林立:菜市口百货商店、电影院、南来顺小吃店、文化用品商店、人民照相馆、新华书店等,所有这些满足了人们所有购物需求,所以老宣武区人购物是很少远足到其他处,西单和王府井大街便少有人去了。这条街如今依旧,较以往也拓宽了很多,但失去了过去的繁华。
宣武门城内,紧邻着城墙是条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叫顺城街,沿着这条街东行可至和平门。这条路段在我的记忆中是十分干净整洁的,与城墙外噪杂的环境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城里与城外的差别。1971年建造地下铁路时,宣武门城楼和城墙都拆除了,今日这里虽界限不再分明,虽还称为宣武门内、外大街,但已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了。记得我首次登城楼时年纪还很小,是父亲带着我去观光的。
不知父亲是工作忙,还是家务事繁多,也可能是晚间到城墙上乘凉目的,每每带我去爬城墙基本都是夏季,且是黄昏时分。那时的城墙顶没有什么安全管理和相应措施,人们可以在城墙上以任意方式自己娱乐,在我的记忆中,放风筝的人居多,有可能高空即使是夏季气流还是较大,便于风筝放飞。
城楼的晚上,楼阁内外有成群的蝙蝠飞来飞去,时而腾空翱翔,时而闪电般向人们飞来,然后擦着耳边飞过。那时从父亲的口中第一次知道蝙蝠虽然有眼睛,但基本看不见什么,全是靠发出的声波遇到障碍返回后的信号辨别前方的障碍物。当年的我并不懂什么是“波”,似懂非懂地记忆着父亲给我的这些解释。儿时曾还听老人们说蝙蝠是老鼠变的,我自幼就对老鼠有恐惧感,无论蝙蝠是否由老鼠变的,蝙蝠的样子也令我生畏。
为满足北京的城市交通的发展,原宣武门城门洞的通车能力已不适应交通发展,尤其是无轨电车出现,需要搭建电线。1955年3月,在宣武门东侧城墙开辟了一个豁口,豁口呈V形式,豁口在今天主教南堂的对面。并在城墙豁口外的护城河上增架了座钢筋混凝土桥,之后,载重车和公交车均从此通行,宣武门城门洞基本是步行街了。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建国10周年国庆那天上午,父亲带着我去观看受检部队行列,我们很早就站在新建的宣武门大桥上等着观看受阅车辆由此驶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国庆礼炮声过后,飞机沿着长安街上空自东向西很低很慢地掠过,紧接着受阅部队的绿色的军车、炮车、坦克车从天安门驶向西单,然后转往南而行,稍东转弯,再从宣武门城楼东新搭建的这座桥上隆隆驶过,桥面、路面上留着坦克车履带碾轧后留下的深深痕迹。
那是我首次见到坦克车,记得坦克车上面的顶窗露出战士上身和头部,头上戴着坦克兵专用隔噪声、护耳朵的厚厚帽子。战士们面容严肃,在我们的注目礼中缓缓驶过,显得那么庄严,那么威武。伴随着坦克车发动机的轰轰声,我感觉到脚下的水泥石桥随着微微颤抖着。
我自幼就有好奇和打探的习惯,看到坦克车是钢铁封闭式的,只有不大的瞭望孔,没有其他窗户,那些坦克车里的驾驶战士是怎样观察道路前进的?我向我心目中的知识“宝库”求解,父亲告诉我,坦克车内有潜望镜,可以观察外面的一切。我相信父亲的知识渊博,那时我并不理解什么是潜望镜,但也没有继续追问。只是站在震颤的桥上,目送着一辆辆带着轰轰响声的坦克车、装甲车、军用卡车缓慢驶过。
护城河
我儿时的南护城河水是活水,自西向东流淌着。那时河水水面很宽,河堤很高,水也还算是清洁,河水中有很多的小鱼及水生植物。每逢夏秋季节会有各种各样的蜻蜓在水面上、在河堤上飞舞,时而高处相互追逐,时而擦着水面尾部点水。河的两岸水浅处有一片片密密麻麻的红色鱼虫和小白条鱼苗,大人、孩子手持用医用
纱布制作成大小不一的捕捞工具(俗称抄子)捞鱼虫或小鱼。
早年的宣武门城墙外东侧与护城河之间的一片空地,每到晚间会有灯光昏暗的餐饮市场,都是些私人的小摊位,经营些价格低廉但很接地气的餐食。傍晚阳光西斜后,就有不少人挑着个担子来到这里,担子的一端是燃煤的火炉,一端是准备出售的各自拿手主食或辅食。条件好一点商户,或买卖也大一点的,运输工具是两轮或三轮的小车。所经营食物具有独家独创性,且都很单一的小吃或正餐。如老北京人喜闻乐道的:炸灌肠、炸酱面、已经失传的抻面和卤煮火烧等。地片并不很大,但环境热热闹闹,天彻底黑下来后,人头在昏暗的灯光下攒动。记得这里经营的都是以面食为主的餐食,劳累一天的人们,在这里坐下来,喝点小酒,再吃些热气腾腾的饭菜,额头、胸前渗出酣畅汗水,确不失为一种享受。
现宣武门城楼城墙、环城铁路、护城河都相继消失了,尽管新颜的宣武门已是高楼、商厦和宽阔的道路,但曾经那个伴随我长大的老宣武门旧貌依旧清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文|黄永顺